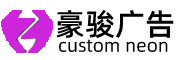霓虹灯发光字工厂需要哪些设备 霓虹灯发光字厂家
霓虹灯发光字工厂需要哪些设备 霓虹灯发光字厂家
大卫·奎曼
几千年来,狮子、老虎和其他大型掠食动物的存在让人类心存畏,它们始终也是史诗和传说的素材,成为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如今,无论是印度吉尔森林的亚洲狮、澳大利亚北部的湾鳄、罗马尼亚山里的棕熊还是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东北虎,这些顶级捕食者的处境已经四面楚歌,可能只存在于玻璃屏障或铁围栏的一端,而我们则高高在上地端详它们。这种变化正在改变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忘记自己和大型掠食动物属于一个生态系统,这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对待它们的方式,我们认识到,人类已经丢失了对这些吃人动物所保有的恐怖,而这种恐怖原本是人和自然的相处之道。
戴维·奎曼(David Quammen)是美国科学、自然和旅行作家,他将目光投入到因人类扩张而在迅速消失的荒野,去坦桑尼亚、印度、罗马尼亚、俄罗斯…… 追踪大型掠食动物的故事和文化,在以这段经历写成的《众神的怪兽》一书中,他反思了人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并对顶级捕食者目前不乐观的处境发出呼吁。
众神的怪兽: 在历史和思想丛林里的食人动物;[美]大卫·奎曼/著、刘炎林/译;商务印书馆;2022-1
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私家地理摘录书中作者在在俄罗斯最好的栖息地追踪老虎的经历,来观察东北虎的存在给一个西伯利亚小镇带来了什么。
在俄罗斯最好的栖息地追踪老虎
俄罗斯最好的老虎栖息地之一特尔尼是个摇摇欲坠的简陋小镇,人口有5000人。外围街区横跨山麓丘陵,小镇中心在平地上。一条名为谢列布良卡(Serebryanka,俄语中“银色”之意)河的小溪从山上向南流入大海。
小镇的主要生计是渔业、鱼罐头业、木材业以及政府事务(特尔尼是县政府所在地,也是锡霍特 - 阿林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所在地)。渔业贸易似乎一直都很稳定;木材业繁荣之下则存在危机;政府不再是过去的样子。
主要由海外非政府组织资助的东北虎项目带来一些额外收入,但没有明显改变市民的态度。当地学校像是一家粉刷过的工厂。如果你仔细搜索,向人问路打探,或者不用霓虹灯的提示就能认出西里尔字母写的magazin这个词,你就会发现门前有着阴暗铁门的几家小杂货店。在这些商店里,你可以买到廉价的伏特加、美味的啤酒、清淡的奶酪、神秘的香肠、巧克力、杏干和美味的腌鲑鱼。4美元可以买到所有你能带走的东西。
特尔尼小镇,谢列布良卡河穿过
小镇的街巷都没有铺装过路面,至少在山坡陡峭的地方是这样。遇上春雨泥泞,简直无法行走,于是铺了木板。木板铺得很随意,就像把废弃的木板直接从脏兮兮的建筑工地上扔下来。勇敢的小平房聚集成不规则的街区,房子的侧面是风化的木板,屋顶是波纹石棉。
在大片灰色和棕色房子中间,有几栋房子刷成明亮的颜色——更确切地说,它们曾经被刷成明亮的颜色。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逐渐暗淡但依然醒目,就像是点缀在单调街区中的奇怪色斑,暗示着苏联涂料供应的变化莫测。曾经可能是黄绿色的颜色,现在看起来更像芥末色。鲜艳的天蓝色已经褪成欢快而平淡的蓝色,就像派对上瘪了的气球和老迈鹦鹉的蓝色。
室内管道在特尔尼很少见。每栋房子60步以内必有一口井。水从井里一桶一桶送到厨房,再送到每周洗澡用的桑拿房中。桑拿房在每个院子的另一个角落,跟到水井的距离差不多。
在西伯利亚的冬天,要为一桶洗碗水或是为了上厕所走60步,可实在是一段很长的路——我现在这么说,既是出于经验,也是出于同情。
当暴风雪来袭时,每个家庭都像是被围困的堡垒。然而,特尔尼人慷慨、热情、开放而亲切,至少当你被恰当地介绍到火炉加热的厨房时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个陌生人,在街上遇到他们,他们只会变得冷漠和警惕。晚上十点就会停电。
这是一个安静而乏味的地方,跟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许多小镇并无不同—除了偶尔有一只老虎漫步走过,在这家或那家停下来,如同死亡天使般杀死并吃掉一条狗。
小镇上的房屋
我在特尔尼及其周围呆了十天,就干了三件事。一是跟在戴尔·米奎尔、科里亚·雷宾和其他人身后,在白雪皑皑的山坡上和凝水成冰的溪流底部寻找老虎的踪迹。二是与当地老虎权威,比如研究老虎和老鼠的叶夫根尼·斯米尔诺夫,谈论科学和保护问题。最后,还见证了老虎和狗之间一边倒的持续冲突。
狗这事让我特别感兴趣。这些犬科动物在老虎和人类的接触面频遭不测,令人不安,代表着更大的紧张局面。然而,这似乎并不完全是坏事。我们都有理由怀疑:老虎吃狗肉到底是一种摩擦,还是一种润滑?
我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来到特尔尼的当晚,米奎尔收到消息,一只戴着无线电项圈的老虎潜入小镇,杀了科里亚·雷宾的一只狗。就在前天晚上,这只名叫迪克的狗在凌晨4点左右开始吠叫,然后就沉默了。第二天早上,科里亚发现它已经死了,而且被吃了一半。迪克剩下的部分(脑袋、脖子和小部分肩部)仍然连着链子。现在好了,老虎杀死了老虎项目王牌追踪者的看门狗—这似乎不仅仅是巧合,不是吗?只要一点点非科学想象的飞跃,就可以将这件事看作报复行为,一种猫科动物的粗暴反击。通过颈圈发出的无线电频率,识别出是年轻雄虎费迪亚,去年11月科里亚曾试图捕捉它。
锡霍特 - 阿林自然保护区风光优美
最初,费迪亚在河的北面杀死了一头牛和一只狗,这引起了老虎项目的注意。野外小组按照标准的捕获和释放流程,在被吃了一部分的牛尸旁边设了陷阱,希望饿着的老虎还会回来。当它回来时,科里亚用装满镇静剂的飞镖射中了它。做完详细检查,戴上颈圈,起好名字,然后当场释放,尽管现场距离特尔尼小镇很近。在接下来几周里,费迪亚渡过这条河,平安无事地穿过小镇,在科里亚房子后面的森林山坡上过得舒舒服服。它一直是只谨慎的好老虎,以野生猎物为食,避开牛和狗的更多诱惑,直到昨天晚上。
听到消息后,我和米奎尔立即跑到科里亚的房子,加入监听行动。这个小组包括科里亚的弟弟沙夏(他也是这个项目的跟踪者)、阿纳托利·霍巴特诺夫(一个表情严肃但温和的男子,留着深色胡子,穿着迷彩背心,手持 AK-47,在政府的老虎反应小组工作)、约翰·古德里奇(一位瘦长的美国生物学家,六年前加入米奎尔的项目)。阿纳托利在迪克的残骸上设置了两枚爆竹和一枚照明弹。这些小惊喜都是绊线触发式的,让冒险回来继续进食的老虎产生可怕的厌恶感。它会屈服于这种诱惑吗?在科里亚小房子的前屋,无线电接收器在费迪亚的频率上稳定鸣叫,就像没有指针的布谷鸟时钟,确信会大声报时,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接收器的信号音色怪异,任何用无线电跟踪动物或在潜艇里收听声纳的人都很熟悉:蒂克……蒂克……蒂克……蒂克……节奏缓慢,音量也挺大,这表明费迪亚已经在附近睡着了。要想知道它是不是已经饱餐狗肉,唯一方法是等待。
那么,我们就等着。但是,像费迪亚一样,我们不会空着肚子等待。这里是俄罗斯。人们已经聚集在一起,怎么会少了食物?在科里亚妻子露比亚的操持下,我们敞开肚子大吃特吃,有红菜汤、胡萝卜沙拉、炸鱼、香肠和鱼子酱饺子。酒足饭饱,我们又坐下来监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蒂克……蒂克……蒂克……蒂克……为了消遣时间,我们开始看电影,朱丽娅·罗伯茨和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塘鹅暗杀令》,不过是俄语配音。这让程式化的好莱坞情节变得更有趣味,因为除了 da 和 nyet,我一句话也听不懂。我们在科里亚和露比亚的卧室里看电影,所有人都趴在床上和地板上。与此同时,接收机还在缓慢而有规律地响着。信号偶尔会改变节奏—加速到蒂克蒂克蒂克蒂克—表明动物在动。这促使科里亚振作起来,拿着那个小玩意出门仔细扫描。用定向天线慢慢扫描,可以精确定位信号的方位。但每次从门外回来,他都带回来不确定的消息—信号又慢了,费迪亚还在休息。我扪心自问,现在是失望还是高兴?大概还是失望,我想。如果不给费迪亚来点粗鲁的教训,它就不太可能改掉吃狗的习惯。此外,我们都渴望来点行动。
但不是今晚。那天深夜,丹泽尔和朱丽娅躲过子弹,躲开倾斜的汽车,避开身穿细条纹西装的邪恶白人。费迪亚对装有机关的半条狗漠不关心。然后我们就散了。这只老虎很鲁莽,但不容易上当。
锡霍特 - 阿林自然保护区的东北虎
第二天,我拜访了锡霍特 - 阿林自然保护区的主管阿纳托利·阿斯塔菲耶夫(Anatoly Astafiev)。听我们说到头天晚上的监听,他提到,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老虎出现在同样的森林山坡上—没错,就在科里亚·雷宾现在居住的地方。它们经常进城。“它们当然吃了很多狗,”阿斯塔菲耶夫说,“有二十几条。”但老虎跟人没有真正的冲突,他补充道,老虎只是稳定地消耗家狗供应,而这种供应似乎也很容易维持和补偿。
几天后,我和沙夏·雷宾一起去追踪老虎。他今年25岁,性格开朗。他和哥哥一样,出生于乌克兰,在一间技术学院接受汽车制造培训,在生产出口重型采矿设备的工厂短暂工作过,之后就来这里寻找更具森林气息的生活。对疲惫和寒冷,沙夏朝气蓬勃的忍耐力令人赞叹,非常适合在这些山区从事老虎工作。他只会说几个英语单词,我懂的俄语更少,所以除了手势和点头,我们几乎不能交流。但这没关系,今天大部分工作依靠的是视觉、听觉和身体。沿着自然保护区里的道路行走,我们在雪地上发现了新脚印。接收机收听到强烈的信号。
“莉迪亚。”他说。
“莉迪亚。”我附和着。沙夏认出了目前佩戴颈圈的五只老虎中的另一只。约翰·古德里奇跟我简要介绍过这份名单,包括淘气的费迪亚和四只雌虎:奥尔加是众人眷顾的宠儿,她是该项目在1992年捕获的第一只老虎;另外三只是内莉、勒德米拉和莉迪亚。除了这五只戴着颈圈的老虎,还有三只雄虎(亚历克、鲍里斯和米沙)和其他几只雌虎。它们来了又走,其中几只被偷猎者杀害。鲍里斯在南部的一个城镇附近遭到枪杀。它当时溜进一个棚子,走出来时被人发现。奥尔加躲开了这些麻烦,运气很好。她现在戴的颈圈已经换过四次电池。费迪亚,如果它不洗心革面,就可能重蹈鲍里斯的覆辙。至于莉迪亚,她现在占据了这片领地。可能是因为有海岸公路穿过,盗猎者很容易进来,这片领地上前几只佩戴颈圈的雌虎已遭不测。
强烈的蒂克蒂克蒂克蒂克声表明,莉迪亚就在附近,就在长满森林的山坡上,或者西边的灌木丛里。一天前她还在路的东边,沿着海边的悬崖潜行。约翰和我跟着她度过了一个寒冷的下午。一夜之后,她似乎穿过公路到了这里。通过无线电追踪她的行动,用三角法确定她的位置,把位置点绘制到地图上,然后徒步检查地面上的标志—她的窝、杀戮的残余以及其他显示其活动的微妙线索—这些都是沙夏和他哥哥每天要完成的任务。这些在野外助手的帮助下收集的证据,让古德里奇、米奎尔和斯米尔诺夫对东北虎如何在栖息地中生活有了形象的认识。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不是什么顿悟。耐力、耐心、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性都是必备的素质。大多是间接的证据,很少能见到真正的老虎。
当我和沙夏开始今天的徒步时,又赶上风刮得很大。在蔚蓝的天空和耀眼而温热的阳光下,风像一根消防水带,把我们身上的热量抽走。我眯着眼睛迎着狂风,品味着一首诗里的两句话。这首诗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每到极其寒冷的环境中,每句话都能给我带来欢乐:
如果我们闭上眼睛,睫毛会冻结,直到我们看不见;这并不是什么有趣的事,但唯一会哭的人是萨姆·麦基。
我们沿着莉迪亚的足迹来回走了六个小时,像雪中的幽灵一样追踪她。当我们刚开始跟着她的足迹往前走时,沙夏有规律地停下来收听接收机。有的地方积雪深及大腿,我们穿着靴子和羊毛裤,每一步都得把膝盖抬得高高的。在开阔山坡上的浅雪中,我们走得更快,但偶尔也会被绊倒,或是在底层干燥而光滑的栎树叶上滑倒。在一些地方,夜风吹过莉迪亚的足迹,脚印的边缘变得柔和模糊,但仍然又深又大,不可能错过。她总能把后脚准确地放在前脚脚印上,所以虽然是四条腿,但留下的脚印几乎不比两条腿多。从脚印的间距来看,她的步伐大小看起来跟人很像。但在溪流中光滑的黄蓝色冰面上,每个脚印都清晰可见,大如葡萄柚,被莉迪亚的重量和热量压印在那里:一个掌垫和四个卵形脚趾。
1970年,苏联的东北虎邮票
我们爬上几条山脊,连滚带爬地向前攀走,随时调整路线。这时“蒂克蒂克蒂克蒂克”的声音越来越响。最后,当我们在一条山脊上停下时,沙夏收听到一个非常强的信号。他断开天线,仍然收到强烈的信号。“三百米,”他指着前方说。“没动。她没动。她是……”他努力寻找合适的英语单词,“……在睡觉?”事实上,她到底是睡着了,还是沐浴在阳光中,或者蹲在巨石后面,窥探入侵她领地的笨蛋,永远无人知晓。
“已经够近了,”沙夏决定,“我们不想让她紧张,对吗?”“对,我们不要那样做。”我同意。于是我们撤退。我们再一次沿着她先前的足迹往回走,追溯她昨天晚上和白天的行迹。沙夏现在收起接收器,完全依靠传统的技能。他给我看了一个莉迪亚在树下留下的气味标记。即使有沙夏的指点,我也几乎闻不到她辛辣的签到标记。他指了指小溪积雪的河岸上的一个小洞,还说了打洞动物的俄语名字。水貂?也许是紫貂?我只能猜测。
我们看到了梅花鹿的踪迹,它们的脚印和一小堆粪便。穿过斜坡332 上帝的怪兽:在历史和思想丛林里的食人动物和山脊,每一步得奋力从雪里拔腿,沙夏艰难地跋涉着。我努力跟上,我在球形的羽绒服里气喘吁吁,汗流浃背。风停了,但午后并没有变暖。尽管我浑身发热出汗,但每当我停下来写笔记,手指就被冻得麻木。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吃午饭。我边走边嚼一些肉干。穿着浅色羊皮夹克的沙夏,什么也不吃,但丝毫没有疲劳的迹象。
最后,我们下到一处溪流底部。那里结满了冰,还有灌木、金黄色的草丛和飘过来的雪。沙夏开始之字形迂回前进,试图切回莉迪亚的路线。他断断续续地找到脚印,跟不了多久又丢失了线索。最后莉迪亚一去不复返。她的足迹被二十四小时的风雪抹去了。我们又走了一个小时。沿着小溪顺流而下,穿过一条应该通向大路的小路。我现在已经精疲力竭,饥肠辘辘,摇摇欲坠。大腿几乎举不起来,脚趾也麻木了。身体只能靠着本能行走,大脑已经不转了。我包里的某个地方还有一点巧克力。我终于瘫倒在沙夏的卡车上,惊讶地发现水壶竟然没有冻成冰坨。这是老虎栖息地中典型的一天。
莉迪亚是一只幸运的动物,而且适应力很强。她的领地横跨特尔尼西南几十平方英里。那里是得天独厚的栖息地,猎物众多,水源丰富,唯一的瑕疵是有条横穿的道路。不过,其他领地可能问题更大。别的老虎可不像她那么远离人类活动区。第二天早上,我和约翰·古德里奇在他家厨房的火炉旁喝咖啡,听说费迪亚又杀了一只狗。
责任编辑:钱成熙
校对:栾梦
Comments are closed.